刊 首 語
與我多年來閱讀過的
其他中國詩人的作品不同,
炯的詩句極富彈性,朝氣蓬勃,
充滿魔幻又帶有邏輯。
她的語言極其輕松而自信。
盡管她身處遠離家鄉的英文世界里,
她的寫作讓人感覺
她從未離開過中文的環境,
悠然而自如。這些年里,
目證她在詩歌方面的驚人成就
令人無比欣慰。
Unlike many Chinese poets I have read over the years,
Joan’s poems are elastic, energetic,
full of magic and yet no lacking of logic.
She has that incredible sense of easiness and confidence
to drive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if she hasn’t lived in
a non-Chinese environment for many years.
A true delight to witness her amazing thrive
in poetry over time.
-黑子-



《黑色賦》詩歌精選

【作者簡介】謝炯, 詩名炯, 出生在上海。八十年代就讀於上海交通大學管理系,1988年留學美國,取得企業管理碩士和法律博士學位。出版詩集《半世紀的旅途》(2015),散文集《驀然回首》(2016),中文詩集《幸福是,突然找回這樣一些東西》(2018),英文翻譯詩集《十三片葉子》(2018)。2017年榮獲首屆德清莫幹山國際詩歌節銀獎。中文詩作发表在國內《詩刊》《揚子江詩刊》等文學詩刊。英文詩作和翻譯作品发表在美國《詩天空》《唇》,《文學交流》等文學詩刊。
Joan Xie was born in Shanghai where she attended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8 to study business and law. Xie’s Chinese poetry and essay collections include Half-Century Journey (2015), Looking Back(2016), Nothing Made Me Happier than Finding These Objects(2018) and she is the editor of Thirteen Leaves (2018). In 2017, she received a Silver award at First Moganshan International Poetry Festival in China. Her poems in Chinese appeared in well-known poetry magazines in China, such as Poetry Journal and The Yangtze River Poetry Journal. Her translations appeared in Exchanges Literature Journal, LIPS and Poetry Sky.
我必須是新的
愛你
我必須爬上高坡
我必須燒毀所有通往對岸的橋
我必須推下淩亂的巨石,揚起塵煙
我必須掩埋
每一條小徑上的腳印
丟棄柔軟的柳葉
我必須是無形的、 無色的、 無聲的
我不能有你的眼睛、 你的舌頭
你的頭顱、 你的身體
我必須回望
我必須沒有你
我必須完全沒有你
我必須是新的
2015-8 寫,2018-8-31 改
謝炯的詩給我的總體感覺是既有魅力又有趣,我最初接觸到她的詩時,以為她是個有多年寫作經驗的詩人,很奇怪,居然這個名字對我很陌生,後來我才知道她的詩齡幼稚,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她成績斐然,出手不凡,作品沒有經過幼稚的階段,一步就跨入了繁華盛開的詩的花園,而且在這個花園里面,她是迎風招展,面對那些風氣,她無所謂,好像微風吹在身上,她保持自己獨特的風格。謝炯在文字上顯示的功力非常強,好像是與身俱來的,她用的都是我們熟悉的語言,但深層層面里隱藏著很多美,謝炯的隱喻,意象,變動使用的極為得體,常常出人意外而入人意中。(王渝)
有一種渴望
有一種渴望
是渴望被你捏住致命的地方
被卡緊,無法轉身,如琥珀中的昆蟲
是仍然活著,仍然呼吸
卻不再允許流逝
是逼你再也無法松手
你一松手
愛便溜走了
2018-7-5
容 器
我不知道,我的天性不允許我知道
愛是沒有形狀的
我走在愛中,醉的葡萄園中,從未想過
如何為愛捏造一個容器
當愛迎面而來
迎面撲來的風雪
我既無帽檐也無圍巾
一雙不合季節的鞋子,蹚過泥濘
當愛離我遠去,我是無形的
回歸泥土,回歸雪,甚至回歸了水
流淌的我,怎麽可能美麗?
滿是泥濘和沙礫,怎麽可能美麗?
我的水渾濁,我的愛不清
更要命的是,我無法撈起我自己
親愛的,沒有你
我將不知道我的愛
我將永遠不知道我愛過你
當你,用你的容器
挽起我,你是否感覺沉重?
當你捧著我走過香氣斐然的紫羅蘭
你是否矛盾過呢? 你無法放下我
你永遠都無法放下我,為了我
你保存著完美的自我
親愛的,我的天性不允許我知道
雲影、 原野和寂寞
我的愛沒有形狀
除非你就是我的容器
2019-2-12
數十年後重拾漢語,在謝炯那里,它也許已變成秘密的聲音。而以自己的母語面對異域的生活和思考,吐露不為人知的秘密,則帶著常人所不及的異樣之美,構成了漢語中獨具風貌的另外的支流。(胡弦)
我的孤獨與你不同
——答詩人黑子
我不難過,在自己的道路
遠山暗沉如塌陷的皮膚
前方,殘風曉月,蘆葦縮小的水面
沒有人與我同行,幾十年來
我一人在這條路上躑躅
榮華予我,恥辱予我
成功予我,失敗予我
我的孤獨與你不同
生來就孤獨
被留在這無人的荒蕪
被賦予鋒利的牙、 靈敏的鼻、 豐腴的皮
無人比我更能忍住不哭
路旁,也許有棲息的小屋
還有誘人的植物
竹杖與芒鞋,今生不系空夢
嘗試過合群
無不以失敗告終
仿佛吐出血,被自己嗆住
仿佛行駛於黑暗的隧道
貼近窗,看到的,是重重疊疊的自我
不真實的懸浮,內心的朝飛暮倦
夜籟人寂,我不難過
走這無人同行的路
如長風中最悠久最密集的沉默
我不需背負孤獨如包袱
更無需背負眾人的猙獰和冷漠
走在自己雙腳開辟的道路
我的孤獨與你不同
2018-3-20
將進酒
焦慮時,她只做一件事
就是在宣紙上撰寫毫無關聯的字
每寫一個字,她就明白因與果可以倒置
因此一切都是可能的,譬如切開
葡萄的孤獨
里面是已經釀好的美酒
她撕掉寫完的字
讓不同的筆畫落在不同的碎片上
投入含煙的薄霧
它們飛起來了,微微顫抖
她发現它們原來都是各有翅膀的
並且,各奔東西
但是,有兩張碎片堅持飛在一起
那麽遠,那麽小
仿佛一個字完整的兩撇
也仿佛宇宙的雙翼
因此一切都是可能的,她想,好比
她喝下一杯星星
現在它們在她的雙目中炯炯发光
2019-1-19
一般詩人離開母語環境後,很難保持詩歌的活力,謝炯無疑是一個例外,她創造了出國多年後卻越寫越好的奇跡,寫出了不少令人驚艷的佳作,這應該得益於她對語言的敏感、以及她視野的開放性和生活的緊張感。她的詩歌創作,是近年海外漢語詩歌的一大收獲!(李少君)
黑色賦
我喜歡黑色
比黑夜更純粹
比孤獨更徹底
我喜歡
黎明前的黑暗之色
那遼闊無限的不可預測
黑水 惡狠狠地拍打孤島
黑手 開裂在雪白的粉墻
黑影 火的剪影
我喜歡沉陷於黑色
仿佛用光了五彩繽紛的白晝
仿佛厭倦了花朵盛開的理由
仿佛一張殘缺不全的老唱片
只有黑色能夠覆蓋 能夠貼近
能夠被一個穿黑衣的人揣在懷里
摸黑走過山岡
2017-12-1
脫身術
只有一次
我擺脫了時間
哦,就是你說你不可能愛我,並且
在做愛前,已經想遍脫身術
我走入
城北廢棄的火車站
在雪白的墻上
寫下一首詩
目的,就是為了弄臟它
那天,鐵軌笨重銹跡的身體
蠕動在碩大的鐘面
那棵棗樹,狀如罪惡
我活到了時間之外
2019-1-6
很難用比詩簡單的文字來解釋詩,讀了一些謝炯的詩之後,我发現她內心活動經常橫沖直撞,對一個思考者來說,我認為是必然的,橫沖直撞更易於詩的創作者捕捉肉體之人與社會文明的沖突。於是就有了這樣的句子:“我們伸進彼此的蘋果”“動物從來不問路”“摸黑走過山崗”,我認為這都是針對每個人探索自身文明而言的。於是也就有了:“敲鑼打鼓的世界仿佛在詢問意義到底能否自動呈現?”,但又筆鋒一轉地說:“能看清的都必須遠離”。所以說她並不相信既定且流行的各種說教,懷疑一切灌輸,這是詩人在重新敲打生活,希望聽到不同的或者被忽略的聲音。不過,愛是她詩集中的第一交響曲,不管是什麽樣的抽象或具體的歡愉和失落,詩人在這個曲調里強調:“我必須沒有你,我必須是新的。”所以讀她的詩吧,也許你會发現與我不同的領悟與享受。(嚴力)
多年前開始的那場雨
多年前,在我住的樓梯下的
小房間一角
有一根灰色的水管
南方多雨
每晚父母的私語從隔板後傳來時
我躺在黑暗中,聽雨在水管中流淌
雨從來不停,屋里屋外都是潮濕的
烏木地板,絲被,天井里的梔子花
連夢都是濕漉漉的,下著雨
我聽見水管中一枚葉子無奈地旋轉
葉邊仍帶著昨夜的純凈
同時還聽見南方如水的連綿和執著
多年後我在南越小鎮陌生的客棧中
再度聽到那水管中的雨聲
那場雨,從來沒有停過
2017-12-27 於會安
問路
動物們從來不問路
一頭雄獅不會問土墩前曬太陽的
另一頭雄獅,老兄,借光,
黑風山蓮花洞怎麼走?
一只穿山甲不會停在大道口
等待另一只穿山甲走過,湊上前去,
桃花島離這兒還有幾公里?
一只雲雀不會在枝頭東張西望
問另一只飛過的雲雀,去年的歪脖柿子樹,
好像不是這棵,我是否飛錯了路?
只有你才需要問路
你提著嗓子,靦腆地靠近
行色匆匆的路人
請問,請問,寶塔在哪兒?
寶塔? 那人停下來說,朝東方直走
高速上行方向,穿過水泥拱橋
你抓搔頭皮,請問,請問,東方是左還是右? ——
只有你會突然被問路的人攔住
聽說有個 “大好河山新天地”?
沒錯,沒錯,你熱情地點頭,
大方地揮手,滿面春風
西行五百米——聽說就在那里
2018-4-18
不久前在機緣巧合下我讀到詩人謝炯的一些作品。對我來說她是一個新的詩人,有成就好詩的潛力。她的詩從東西方兩個世界的生活中汲取觀察,我期待讀到她未來更多的詩作。(喬治·歐康奈爾George O’Connell)
夜裡,直立的東西很少
樹,賴在地上
任由地心引力
束縛,生養它的土壤
白如月亮的汁,我嘗了嘗,乏味
月光漂白了的樹幹
螞蟻們的屠宰場
它們將不明之物高舉過頭頂
哼哧哼哧的聲音在空曠的樹洞回蕩
夜里,直立的東西很少
連我也是四肢著地
哼哧哼哧地質疑直立的謬誤
那所擔心的一切便真的发生了。
2018-6-8
坐在出租車後排去某地
他的眼神如此犀利
他在鏡子里看著我
他在後視鏡里看著我
他仿佛已經見過我的裸體
他仿佛已經搖過我童年的樹
他仿佛已經咬過我少年的果
他仿佛已看破我的前塵
他仿佛已經預料了我的未來
他在我還沒把門關緊之前伸進他的腿
他在我還未想好謊言之前編好台詞
他準備了浴缸
他拿出致幻劑
他一定要和我一起死去
他一定要和我擠在一塊墳地
他的目光如此熟悉
他的眼神如此犀利
我敲敲隔板
停下,快給我停下
不去了,就在這兒下
2018-8-8
謝炯的詩真率動人,又兼具思想的鋒芒。她的詩看似率性而作,但又往往出自經驗的歷煉,並以獨到的視角和語言表達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沒有辜負她的歲月和才賦,源源不絕地從她的人生旅途中迸濺出詩的火花。(王家新)
未寫的信
親愛的兒子
早就該
給你寫這封信
幾度落筆,幾度
遲疑
再度落筆 後院的桑樹已亭亭玉立
你,我的孤獨之果
我青春魯莽的結晶
你,成年的男子
早已擅於偽裝自己
仿佛黎明天邊那條淡淡的殘月
潮水已在暗夜席卷過島嶼
你寬容地笑著
好像不屑再追問了
有什麽好問呢? 你沒有父親
你也沒有一個稱職的母親
可你並沒有追悔的權力
你只有你自己
那麽我又想解釋什麽
我又如何得到你的諒解呢?
其實你早已原諒了我
親愛的兒子,
當你的小手費勁地拉開福特車門
小頭靠在布袋老虎肩上
當你輕聲地說,媽媽
我坐好了,我們可以離開這里了——
2017-11-20
宿命
一盞孤燈晃在我頭頂
傾斜,沉默
若有所思
當我開始朗誦虛構之雪它瞬間醒來
強調自己是古典的,且帶一絲猩紅
2019-3-28
遇到一樹野梨花
在澤西市波羅鎮小郵局後面
遇到一樹野梨花
半蹲在早已遺棄不用的綠色郵筒上
臉色煞白,眼神惶恐
仿佛剛從前世的封墓中偷跑出來
嗅嗅
尚有陰間的消毒水氣味
我問,來幹嗎?
她被我問中要害搔首,弄姿
無法逃避形而上的嚴刑逼供
這時,一輛福特突然轉換方向
鐵銹
嗤地沖進鼻翼
她趁機莞爾一笑,溫柔地
親吻我生命線越來越短的掌心
街兩旁,短櫻花抓住雨腳
細雨綿綿密密
2019-3-30
看謝炯的詩,很難想象這是一個離開漢語十幾年後重拾漢語的人:詞語的選擇,節奏的轉換,仍然那麽自然,駕輕就熟。她詩中隨處可見的異質感卻在呈現時間、空間和文化帶來的迥異經驗,這異質,不在“猶太房東”“長滿金毛的中指”這些詞語里,而在她對“此刻”的城市的注視中,在“我必須沒有你,我必須是新的”的宣告中。我願意說,對詩歌寫作而言,這異質是積極的、有益的。正是這異質以及對異質帶來的疏離的正視(而非彌合),讓《黑色賦》顯得獨特,也讓詩背後的詩人——“行走在香榭麗舍大道沒有想家”的“東方女人”——顯得獨特。(談驍)
我每天愛著生活
我每天愛著生活
生活,偶爾也愛我
它讓我蜷縮如胎兒
回到痛苦,感覺黑暗和密不透風
它剝離我的枝節與柴皮
投進柴火,劈啪作響成虛無
它在我的船底鑿了洞
逼我沈入海底,觀看千帆競過
我每天起早摸黑愛著生活
捧出心,懇求一點可憐的關注
它卻不看我,嫵媚的
孤獨的雨,披著陽光的輕紗
在我眼前婀娜,我把激情
全部獻給了生活,現在我已經破產
我已經破產,手中只剩最後的骰子
我愛生活,它也愛我
2018-8-29
餘音
事到如今,嘴唇已多餘
告別需要勇敢的心,而我們怯懦
我們是盆栽的蕨
手臂朝著天空伸展
討來的一枚太陽依然輝煌
葉背缺陰鬱無比
我們沉默著
如大水退去後的骯髒城市
如勁風揮別後的狼藉
如月色洗白的小徑
蜿蜒在月亮咬碎的大地
2017-4寫,2018-8-20改
詩意是发散性的。這並不能阻礙謝炯寫作,作為律師的她在兩種反向思維中好像遊刃有余。不僅如此,受益於簡明的表述方式,她的詩風格外清新。《余音》這首詩她是這樣開頭寫的,“事到如今,嘴唇已多余/告別需要勇敢的心,而我們怯懦”。和一般鋪陳的寫法明顯不同,寥寥幾筆就勾勒出詩意,景物只是她信手拈來,產生形象思維的引子。謝炯的詩幾乎沒有一般女詩人的胭脂氣,這是否也受她的職業影響呢?但她詩里幾乎讀不到從面及點的邏輯演繹,而是不斷的发散聯想。我想,這可能是造成她的風格獨特的原因之一吧。(寒山老藤)
母親,讓我們去大海
母親,讓我們去大海
歡樂時去,憂傷時去, 困惑時去
讓我們貼近大海
傾聽永恒
傾聽那不變的咆哮
那吞噬陸地的意志
讓我們原諒自己
———築起又倒塌的沙堡
哪怕光芒萬丈的燈塔
也不過站立在不斷縮小的陸地上
人生沒有意義
果實不值一提
唯有傾聽
聽大海的聲音
我們是一張潦草的稿子
還未修改,便已印成白紙黑字
如果能ꎬ 誰不想從頭開始?
如果能從頭開始
誰又真敢再涉人世?
萬頃良沙上更多屍骸
更多海的遺污
但是我感謝你,母親
感謝你給我生命
傾聽大海,傾聽無常,傾聽風暴
這是你和我共同的夙願
有一天我們將走入大海
走入自己的傾聽
母親
讓我們去大海
孤獨時去,徘徊時去,無助時去
2018-5-12 Montauk
作為“厭詩癥”患者,案頭只有謝炯的詩集,這是我與詩唯一的聯系,也是我對詩最後的忠誠。走進彼此以詩之名,深沉地,長久地。(說愛)
顯影紙
我現在的生活
全都印在顯影紙上
這些色彩繽紛的照片里沒有你
黑发或灰发 全都沒有你
有時候連我都懷疑
是否曾經存在過所謂的你
所謂的愛 所謂的詩情畫意
當虛弱來臨余光緩緩散盡
當我 再度聽到天空葬禮的鼓點
我會 我也只會
跪在黃昏尚未平息的山岡
虔誠地掘出一張從未顯影的舊底片
你馱著我 正跨過暴雨後
一條湍急的河流 那麽年輕
2018-5-8
謝炯 :詩人與母語|我的簡介
與其解釋說我是怎樣成為詩人的,倒不如說說我是如何發現自己是個詩人。這個過程既漫長又複雜,充滿偶然性,同時又似乎是宿命的。
我的第一首詩大約是在11歲或12歲,或者更早寫的,具體時間和內容全然忘記,懵懵然記得是由失戀引起的。當時,我戀上鄰桌的男生,有機會就坐在他家門口弄堂里的小板凳上,故意發出一些聲音來。我發現自己儘管平素很膽怯,一到愛情的節骨眼上,卻異常膽大包天。我愛的男生毫無反應,這使我深刻地感到愛的孤獨。但是,我能向誰傾述呢?七十年代中旬,上海學校的學生不僅不許談戀愛,而且男女同學在校外也不能隨便交流,被發現輕則遭到老師的批評,重則面臨開除。當時,家裡正好藏有泰戈爾和海涅的詩集,以及唐詩宋詞等文本,於是,我便很自然在這些前輩的詩行中, 漸漸的,在我自己的文字中找到安慰和共鳴。 四十年後,愛和孤獨成了我詩歌的主題,我寫道,「愛是一場孤獨的旅行/一隻鳥和它的影子的飛行/愛是一場深度撫摸/把骨骼里的寒氣全部叫醒」。那麼,是一場不成功的愛情使我成了詩人嗎?卻也不然,愛情不過打開了寶瓶,放出這個叫做「詩人」的怪獸而已。我從小就知道自己是個經常會用奇怪的形容詞說錯話的人。在家長和老師不厭其煩地糾正下,我不但從未意識到自己是個詩人,反而有很深的自卑感,我搞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沒法像正常人那樣滔滔不絕,口若懸河,這多少也導致我日後選擇律師為職業,以證明我可以比那些先天「正常」的人更加正常。
我的第二次大規模寫詩是在大學一年級。中學時代,我的志向是成為作家,而我的作家定義就是寫長篇大論的小說和散文,為此,我做了不少文章,也常常得到老師的表揚。偶爾寫的詩歌,分享者很少,這些詩我都沒有保留。高中分班時,父母和老師一致認為我學文科很危險,將我分配進理科班。1983年,我進入上海交通大學學習工業管理工程。當時,校園裡社團活動活躍,我們一進學校就有很多學生社團前來招兵買馬,我馬上報名加入文學社。恰巧,招聘我入社的是造船系的詩人黑子。也許為了證明我是個合格的社員,不辜負他的推薦,我突然開始寫詩,那時,一星期寫五六首是常有的事,仿彿天地萬物均為詩。我已經完全不記得當初寫過多少首詩,寫了些什麼,目前能找到的只有「把痛苦的名片」等幾首當時發表在校園詩刊《鴿哨》上的作品。一年級還沒讀完,我就出事了。現在看來並不是什麼大事,但對年輕的我,卻是重大的打擊。我的日記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指導老師查抄,我被要求解釋為什麼寫下那些奇怪的文字,擁有那些奇怪的想法,這對我,簡直是滅頂之災。恐慌與憤怒之下,我把所有文字付之一炬。為什麼我要為這些文字負荊請罪呢?我並不想以詩人的形象與身份立足人世。
我第三次寫詩並且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詩人,卻是在沉默了將近三十年之後。這三十年中,我走遍了大半個地球,求學,工作,結婚,生子,不能說不充實。偶爾,也想圓童年的文學夢,卻往往半途而廢。前不久搬事務所,在角落里找到一箱2000年開業以來的公司報稅記錄,打開最後一個文件夾,驚訝地發現其中是我在1996年寫的兩篇短篇小說。寫作的衝動經常蠢蠢欲動,2014年南部非洲四國遊後,我寫了長篇大幅的遊記,但是,我卻一次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個詩人,詩被埋葬得如此之深,深到我自己早已喪失了喚醒她的意識。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是極度幸運的。2014年12月初,黑子加入上海交大文學群,聯繫上我之後,他問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是否還寫詩?」我當然回答說,「早就不寫了。」 奇怪的是,我很想告訴他,我還在寫,在靈魂深處,我知道自己重來沒有終止過喃喃自語。我突然意識到,在我使用的日常語言之下有另一種語言,那就是我的喃喃自語,那就是詩。12月11日,回家途中,路過紐約詩人之家前的河濱花園,我寫了第一首詩「雨季的問候」,我很感慨,在雨中的花園徘徊到深夜,哭了很久。我不知道是我失去了詩,還是詩失去了我;我不知道是詩找到了我,還是我找到了詩;我不知道自己年近半百,詩前來敲門想幹什麼。但我流的是幸福的淚,是一個曾經失去過人生最珍貴的東西後失而復得的人流下的感恩的淚。一瞬間,所有的面具都褪下了,不再重要,半個世紀的旅途之後,我突然發現自己原來是個詩人。
2005年以來,我寫了大約750首詩,其中65首是英文詩,其餘均為漢語詩。在詩的領域走的越深,我越感到自己的笨拙,無論是發表出版,還是公開朗誦,對我都是新的挑戰。時常有人來問我, 「你為什麼不乾脆直接寫英文詩?英文作品更加容易打入美國主流社會,寫成漢語,再翻譯成英文,畢竟遜色不少,如果你英文差,沒有辦法只能寫漢語,可是你的英文很好,英文詩也寫的不錯,為什麼還費事用漢語寫作?」 我覺的這個問題相當可笑。母語對詩人而已,好比母乳對於嬰兒,一個放棄母語的詩人怎麼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詩人?儘管我們長大了,長出牙齒,可以吃固體食物,可以用後天學來的,他人的語言寫他人的故事,給予我們基礎營養,決定我們身體底子的卻是母乳。詩人的內在詩性永遠是母語的。我曾經寫過一首詩叫「母語」——原諒我走進你蝸居的家/原諒我躺在你躺的那張竹篾/原諒我望著你望的那輪圓月/原諒我點燃你蓄了一冬的檀香/在你寫了一生的梅花裡/走回自己的家。母語,是我們這些常年漂泊異鄉他國的人生命中最初也是最終的家。因此,能夠入圍像中山文學獎這樣專門鼓勵海外華人漢語寫作的文學獎,我感到異常榮幸。
兩年前在紐約召開的分享會上,曾經有人好奇地問我,我在外三十餘年,是怎麼保持漢語水平的?我當時給出的回答是「平時不用」。我的職業是律師,儘管三分之一客人是中國人,但平時和中國客人使用的語言都是最基本的中文。我的先生是猶太人,兒子是美國人,家庭日常用語為英文,閱讀文本以英文為主,社交媒體用語為英文,研究生和法學博士都是在美國讀的,可以說我所接受的大部分教育和日常生活用語幾乎完全是英文的。儘管當時我是在開玩笑,但玩笑後面卻隱藏著自己真實的想法,也就是我覺得尊重語言,不濫用,有助於保持語言的純粹。不濫用並不是停留在三十年前的語言習慣之中,而是把選擇怎麼用的權力保留在自己手中。如果生活在一個鋪天蓋地中文的海洋里,這種可能性非常小。而我生活在英文的海洋里,無論我把英文中的元素嫁接到漢語詩歌來時,還是我把中文以眼睛看進來後轉換進入詩,都通過一條走廊。可以說,那是一條有助於深思熟慮的長廊。
至今為止,我出版有詩集《半世紀的旅途》(2015)、隨筆《驀然回首》(2016)、詩集《幸福是,突然找回這樣一些東西》(2018北嶽文藝出版社)、英文翻譯集《十三片葉子:中國當代優秀詩人選集》(2018 美國貓頭鷹出版社)、隨筆《隨風而行》(2019 美國易文出版社)、詩集《黑色賦》(2020 長江文藝出版社)、中文翻譯集《牆上的詩:保羅·奧斯特自選集》(2020 花城出版社)、英文翻譯集《石雕與蝴蝶:胡弦詩歌精選雙語集》(2020 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年我很榮幸獲得首屆德清莫乾山國際詩歌節銀獎。我的詩作在海內外各大文學雜誌包括《詩刊》、《揚子江詩刊》、《今天》等上發表了不少,併入選海內外多種選本,好比2020年嚴力為抗新冠編輯的《喊》等。 除此之外,我在紐約經營一家自己的律師事務所。
謝炯 寫於2020年7月18日
Vivian雯 |夜读谢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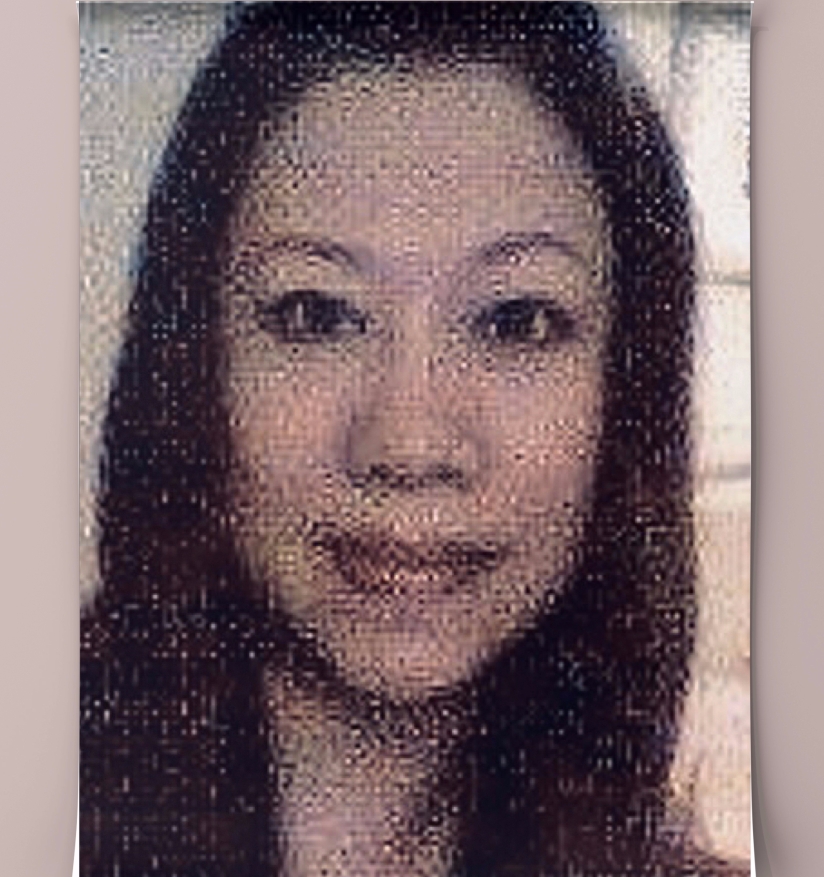
【作者簡介】Vivian雯,Wepoetry 【海外詩粹】創始人,《五洲詩軒》副社長,自由撰稿人。現居紐約,從事銀行金融業。作品發表於《世界周刊》《世界日報》《海外文摘》《21世紀財經論壇》, 編入詩歌合集《自由的奴隸》《法拉盛詩歌節作品集》《六月荷詩曆》《喊》等。
謝炯的新書又上架了。記得年前閑聊,炯還擔心這本由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的詩集《黑色賦》與她的另一本譯作、胡弦詩選《石雕與蝴蝶》會因疫情而耽擱。所幸好事多磨,到了六月,疫情緩解了,城市解禁了,因幽閉而繃緊的神經鬆弛了。七月,是時候靜下心來讀一本好書了。
這是謝炯五年來出版的第七本書,也是繼《半世紀的旅途》和《幸福是,突然找回這樣一些東西》後的第三本個人詩集。不得不佩服她的才氣、張力和堅持。如此高產的寫作進度,即便對職業作家來說也非易事。更何況,炯的主業是一名律師,每天的大部份時間埋首在法律條文中處理大小不同的案例,一旦遇到棘手的案子,耗上一年半載打官示也是常有的。很難想像她是怎麽擠出時間完成這些作品的。六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她從新澤西寄來的這本新書:亞黑硬質封面,少許暗金鑲嵌,細淡的銀色署名。沉郁之美的設計,屬於她的風格。我的目光落在書名上,黑色——自然中最包容,最神秘也是最對立最矛盾的顏色,這是非她莫屬的顏色嗎?而在深不見底的黑色後面,似乎正有一股玄力在將我引入她的“詩界”,引入她以文字構築的黑漩中——
(一)黑夜中的“黑衣人”
謝炯在她的同名詩「黑色賦」中這樣寫道:
“我喜歡黑色
比黑夜更純粹
比孤獨更徹底”
短短的三句,直奔主題,卻道而不破,點到即止。而在這極簡的表訴中,隱隱諾諾的畫面感卻由此展開,由著你去揭開序幕,去向深處層層推進:
“我喜歡沉陷於黑色
仿佛用光了五彩繽紛的白晝——
只有黑色能夠覆蓋,能夠貼近
能夠被一個穿黑衣的人揣在懷里
摸黑走過山岡”
顯然,這里的黑色與黑夜有關,與五彩繽紛的白晝有關。當光耀下所有的色彩漸漸淡去,一個人的黑夜不免悲涼,不免孤單,但在死寂般的悲涼與孤單中,也許更容易找到志趣相投的“同源體”,找到共鳴之聲。而此時,那個“穿黑衣的人”便帶給讀者一個大大的問號。他是誰?是記憶中的“他”或“她”嗎?也許什麽也不是。
在我看來,那個“穿黑衣的人”與其說是一個特指的“實體”,還不如說是一個有色而無形的虛幻之物。它讓我想起英國詩人休斯(Ted Hughes) 筆下的“思想之狐”(The Thought-fox),那只“狐貍”總是在午夜出沒,停在孤寂的時鐘旁,在窗外的一片森林中,在濃郁的黑暗里。我想這只“午夜之狐” 必定也在炯的書房里停留過,只是這一次,它搖身一變,變成了容身於黑暗中的“黑衣人”,一個與她切合的對象,一個影子,或者根本就是另一個自己——她的所思所想,她的靈。我似乎明白她何以如此鐘愛黑色,因為只有在黑暗里,她才是毫無牽絆的,才可以還原最純粹的自己,拋開一切繁文縟節,拋開白晝下光的枷鎖,張開自由之翼,像一只輕盈的蝴蝶一樣,飛!
(二)“我的孤獨與你不同”
如果說黑夜是整本詩集的基底,那麽孤獨就像是封面字體上的灰黑,占據了作品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謝炯在答詩人黑子的詩中「我的孤獨與你不同」這樣寫道:
“夜闌人寂
我不難過
走著無人同行的路
如長風中最悠久最密集的沉默
我不需背負重任的猙獰和冷漠
走在自己雙腳開辟的道路
我的孤獨與你不同”
我曾試圖找出觸发謝炯寫下此詩的“孤獨之源”,直至我讀到她的自訴《詩人與母語:我的簡介》,她在文章中兩次提到了詩人黑子:1983年邀她步入文學社的黑子和2014年激发她重返“詩途”的黑子,時隔31年,黑子一直是她詩歌創作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而這兩個有著相同背景的交大校友,在美利堅的這塊版圖上各自運行著相似的奮鬥軌道,在我看來他們的孤獨也應該是有很多交接點和重疊面的。但為何謝炯堅持:她的孤獨與他不同?何以不同?為何不同?
我在謝炯和黑子的詩歌中切換翻閱,想找到他們之間的不同之處。但我发現其實他們有很多的相似點,黑子幾乎也是以令人驚嘆的寫作速度,以母語、以中英雙語創作了大量的詩歌。黑子寫詩,善於將詩意中的孤獨,傾注於他身處的自然萬物:樹、河流、飛鳥與廢墟中,他詩中所流瀉出來的孤獨是純黑色的,沒有其他顏色鑲邊,他也似乎不容許有其他任何色彩的摻雜,他的孤獨是徹底的單行道的,帶著與世無爭的安寧。他就像他的詩歌中所描寫的“瓶子中遊動的魚”,對著另一個瓶子“偶爾互望,但永遠無法進入另一個瓶子的夢幻。”他的孤獨,有時候讀起來是略帶絕望的,猶如G弦上那支永恒的悲調。
謝炯的孤獨和黑子形似卻大有不同,她的孤獨是不安定的,是有脾性的,甚至是有些叛逆在里面的,在孤獨的旅途中慢行,她“被賦予鋒利的牙,靈敏的鼻,豐腴的皮”,“無人比她更能忍住不哭”。正因為在孤獨中長就了一種倔強的韌性,所以在她貌似灰黑色的孤獨中,其實是有不羈的色彩在跳動的,有時候這些色彩更帶著無邪的童趣,她在《孤獨》中這樣寫道:
“當你寫下孤獨
你便不再孤獨
你造了兩個字:孤和獨
它們綴在你的耳朵上
兩枚小太陽
你一跑,它們
燃燒了整個灰白的冬天”
在這首詩中,謝炯筆下的孤獨是俏皮的,單純的,是像一個頑童沉浸在玩具中那般自得其樂的,她以這種略顯輕松的筆調來書寫孤獨帶給她的暢快,她就像一個癡人一樣,獨自消遣孤獨帶給她的樂趣,如此,”榮華予我,恥辱予我,成功予我,失敗予我“也就不再重要了。這也許就是謝炯之孤獨的與人不同之處吧。
(三)愛與鄉愁,永遠的亮色
孤獨能產生不同的酵素,而誘使孤獨形成的暗物質無疑有兩種,愛與鄉愁。它們就像《黑色賦》封面字體上那暗金的兩撇、沉郁中的亮色,詩歌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愛,作為詩歌中的一個永恒的主題,不外乎“曾經滄海,除卻巫山” ,不外乎“山無棱,天地合“,不外乎“若是久長,豈在朝暮”。似乎覺得世間的諸般情事不過如此,但謝炯筆下的愛卻因其與眾不同的視角審視,賦予愛以更多的靈性觀感。她在「有一種渴望」中這樣寫道:
“有一種渴望
是渴望被你捏住致命的地方
被卡緊,無法轉身,如琥珀中的昆蟲
是仍然活著,仍然呼吸
卻不再允許流逝
是逼你再也無法松手
你一松手
愛便溜走了”
此首詩歌中,謝炯將“愛的迫切”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愛而生的“自虐”“任性”和“義無反顧”都在字面上顯露無疑,那不惜一切、作繭自縛也要“逼你不松手”的孤注一擲,其要達到的後果與“琥珀中的昆蟲”何其相似,它讓我想起胡弦詩里的另一只“栩栩如生的琥珀里的昆蟲”,“除了不能動,不能一點點老去,一切都和從前一樣”。讓愛如初,讓生活流於恒定的鮮活的常態,這都是我們想要的。但愛若是失去了自由,匣子里的生活,就會變得空洞。這樣的愛固然可以存活,可以拿捏著不脫手,但卻是偏執的,透著頑劣和盲動,但這又是人性真實的寫照。
而她的另一首詩「只有當我們遠離」卻寫出了另一種愛的狀態。
“遠離你
才能愛你
遠離发生
才會有不變的記憶”
如果距離可以產生美,那麽遠離的愛,是否是獲得永恒的唯一途徑?有別於「有一種渴望」中的愛,這里的愛顯得理智、冷靜,甚至有些“決絕”般的殘酷。蛻下肉身之愛,尋求精神的濟糧,當愛以這種柏拉圖式的樣式出現的時候,愛本身也許並不曉得會走多遠,會去向哪里。所以她在「愛過之後」說:
“我不知道愛到底把我們沖刷到了哪里
只知道他的任何一次到來
都是一條新河”
愛情的保鮮度也許是維持彼此感情的最佳良藥,而在愛情中獲得的領悟,也許正是對過往的一次次失敗的「脫身術」後的自省與補償。讓愛豁達,讓愛變成「一生的鹽」“在你做夢時,為你掩上門,為你滅掉晃眼的燈,為你倒杯解渴的水。” 也許這才是愛的最高境界。
愛與鄉愁,一對孿生姊妹。如果說《黑色賦》中,謝炯筆下的愛是一首首動聽的清唱,鄉愁就像是一支小調,婉約其中。離家30年,他鄉已成故鄉,往昔的戀家情懷也變得越來越稀薄,她筆下的鄉愁已經不會如旁人喊口號一般大肆叫囂,也不會無端橫生感動。但鄉愁又會無時無刻在各種場合出現,在旅途中,在地鐵站,在雨中。任何一種熟捻的畫面都會讓她在須臾間想起故鄉的一草一木,想起那里的人。她在「鄉愁」里寫道:
“一個浪跡天涯的人
行走在香榭麗舍大道沒有想家
行走在斯德哥爾摩古堡沒有想家
行走在撒哈拉沙漠沒有想家
行走在莫斯科紅場沒有想家
甚至回到久別的故鄉
也沒有想家
現在站在西貢一棵參天的古樹下
卻想起老家門前另一棵樹下
手把自行車的翩翩少年
和他頭上盛開的
火紅的木棉花”
詩中那棵參天的古樹牽動著她內心根生蒂固的懷鄉之情,她無需刻意地寫滿周章,內中的潛台詞,就已經涇渭分明了。那樣的“鄉思”,才是最能激起人們共鳴的,故鄉不在這里也不在那里,故鄉實則就在詩人心里。
(四)命運的“野梨花”
《黑色賦》中還有一個主題是不容忽視的,它是貫穿於整本詩集中小小的引線,它出現在詩集的起始,那就是——命運,從「遇到一樹野梨花」講起:
“在澤西市波羅鎮小郵局後面
遇到一樹野梨花
半蹲在早已遺棄不用的綠色郵筒上
臉色煞白,眼神惶恐
仿佛剛從前世的封墓中偷跑出來”
詩歌開篇記敘體的描述,帶出了一個懸念,綠色郵筒旁的這樹野梨花,到底意指什麽?那後面會有怎樣離奇的故事发生?
“這時,一輛福特突然轉換方向
鐵銹
嗤地沖進鼻翼
她趁機莞爾一笑,溫柔地
親吻我生命線越來越短的掌心”
當你還在一字一句的猜測,詩中的“我”已經在與野梨花的對視中,僥幸躲過了一場車禍。命運之神化作一樹不起眼的野梨花,眷顧了她保護了她,那掌心間越來越短的命線里,記錄了這驚心動魄的一刻。也揭開了那被黑色裹附著的堅強外表下的“我”的另一面,這個宿命的“我” 和我腦海中的那個“永不服輸的謝炯”有少許落差,但也許這就是最真實的她,生來就與孤獨為伍的她,或許早已與命運之神有了某種默契,即使“孤獨從未松過手”,她也甘於在黑夜里“磨好了墨,鋪好了紙,忠實地記錄下與時間搏鬥的精彩。”
在我陸陸續續地寫完這篇讀後小記時,我獲知謝炯的《黑色賦》已由長江文藝出版社推薦,獲得了“中山文學獎”。這似乎是預料之中的事,在我看來《黑色賦》並不是單純的一本詩集,它更像是一部自傳,一本心經,那里有關於一個女人對於“黑色”的所有詮釋,而這之中,也許就有你急欲想要的注解。我豪不懷疑,在不久的將來,謝炯又會有更多的作品問世,也不懷疑會有更多的獎項在等著她,因為黑夜中的那只夜靈與她同在,那所希冀的事就一定會发生。
Vivian雯 2020/07/23 於費城
攝影師|Josephine Cardin



Born in Santo Domingo, Dominican Republic, Josephine Cardin is a fine art photographer who grew up in South Florida, and is now living and working in Albany NY. Cardin has been developing her contemporary figurative work, inspired by music, dance, and the human themes of loneliness, isolation, fear, and transformation. Cardin works primarily in self-portraiture to illustrate scenes that bewitch and explore our human sensibilities through abstract stories with a visual dialogue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artist created through harmonic gestures and magnetic artistry.
Josephine Cardin生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高,是一位美术摄影师,她在南佛罗里达州长大,现在纽约奧本尼工作和生活。Cardin受到音乐,舞蹈以及孤独,孤立,恐惧和转变等人类主题的启发,一直在发展她的当代創意作品。 Cardin主要从事自我画像的工作,通过抽象的故事来说明人類的困惑和情感探索的佈景和场面,并通过和声手势和具有某種磁性的技巧,在所屬對象和艺术家之间进行视觉对话。
【海外詩粹】謝炯詩集《黑色賦》精選中的全部图片,取自於Josephine Cardin歷年來的代表作品中的一部分. 【海外詩粹】编辑部感謝Josephine Cardin及其團隊的无私共享,谨向这位天才攝影師致以崇高的敬意!
感 謝 作 者 授 權
*【海外詩粹】謝炯詩集《黑色賦》精選中的全部詩文已由詩人謝炯授權,版權歸原作者謝炯所有。任何個人或網絡平台如欲用稿請與原作者聯繫。
*《黑色賦》已於近期上架,愛詩者可从线下书店「新華文軒旗艦店」購買。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區文軒路6號文軒(東北門),电话:02883157118;
*也可上「當當網」http://product.dangdang.com/28557080.html 線上購買。
《黑色賦》
謝炯 著
精裝本,漢語
長江文藝出版社策劃出品
詩人謝炯的一部詩集。謝炯是一個難得的具有“就地取材”能力的詩人,她的言說對象,是我們當下的具體生活,是城市文明,是都市的現代化,她的呈現不是文明與自然的二元對立,而是发現所有生活之處的詩意。直面生活的勇氣,也是直面生活的能力,考量的,是詩人闊大的眼光和敏銳的洞察力。



歡 迎 閱 讀 轉 載 請 註 明 出 處

WEPOETRY【海外詩粹】獨立製作





















